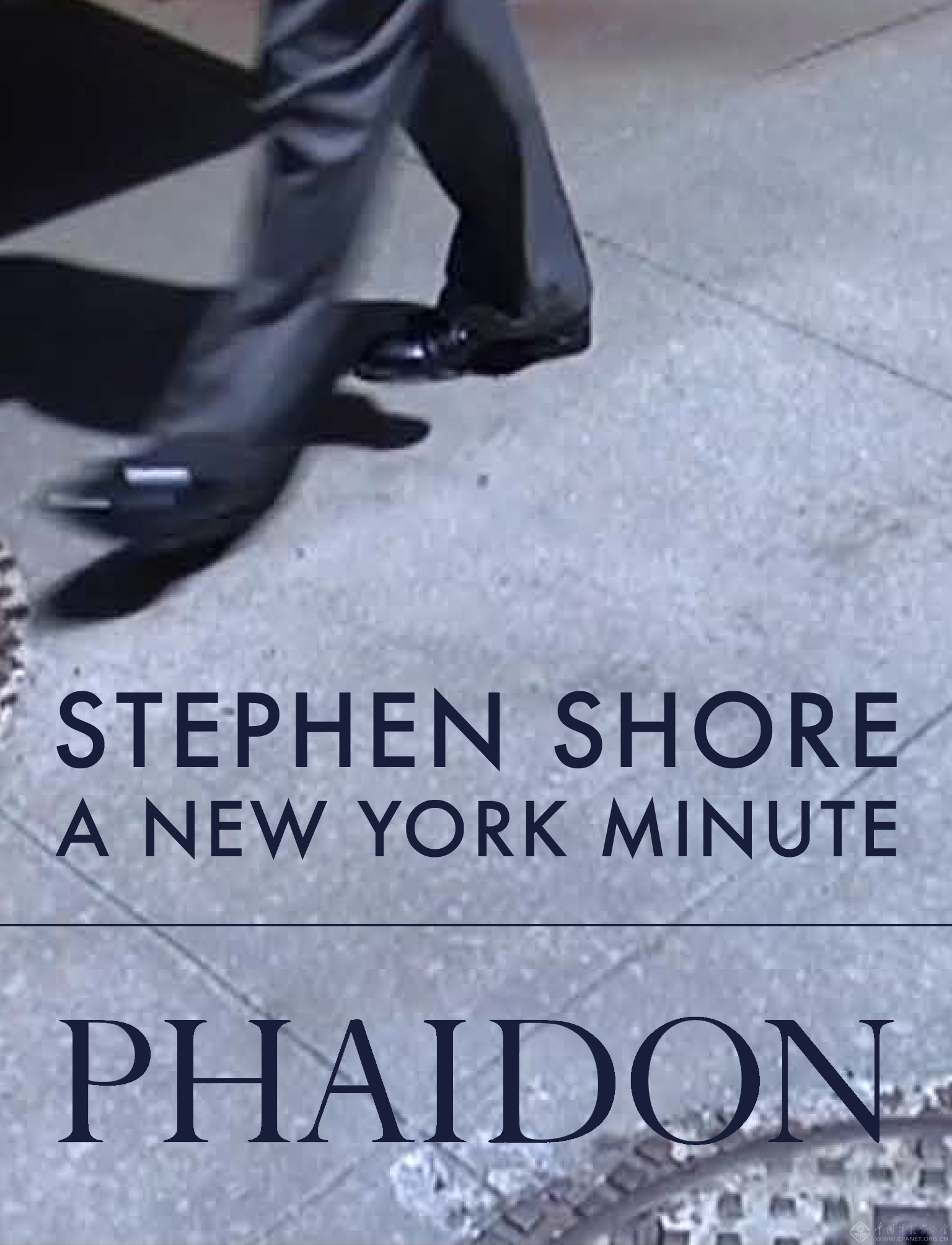
2013年,英國專門出版視覺藝術(shù)著作和畫冊的出版商菲頓(Phaidon)推出了美國“新彩色攝影”創(chuàng)始之一著名攝影家斯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1947~)的首部數(shù)碼視頻電子書,題為《紐約一分鐘》(A New York Minute),在業(yè)界產(chǎn)生重大反響。大家在納悶為何這位年近7旬老攝影家仍要嘗試最新媒介?為何一位擅長用大畫幅相機(jī)拍攝靜態(tài)照片的攝影家會去使用視頻媒介?他的視頻作品與時下正流行的視頻作品有何不同?事實上,肖爾自年輕出道以來,便一直在打破常規(guī)超越自己。
始終要打破常規(guī)
1970年代中,肖爾曾與另一位美國著名風(fēng)景攝影家安塞爾·亞當(dāng)斯(Ansel Adams,1902~1984)共進(jìn)晚餐,席間,肖爾親眼看到亞當(dāng)斯喝下六大杯伏特加烈性酒,之后,亞當(dāng)斯仿佛是在告誡肖爾這位年輕藝術(shù)家,冉冉自語地說,“我在1940年代的創(chuàng)作曾經(jīng)火過一陣子,之后,就一直在重復(fù)自己。”這次與亞當(dāng)斯的邂逅和對話讓肖爾頓悟,促使他從年輕開始就立志不要像亞當(dāng)斯那樣,而是始終要打破常規(guī),包括自己的常規(guī)。
肖爾深受開創(chuàng)了美國“紀(jì)實性”攝影傳統(tǒng)的攝影家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1903~1975)的影響,尤其是埃文斯在1938年出版的《美國照片》(American Photographs)畫冊。該畫冊匯集了埃文斯早期用135相機(jī)拍攝的紐約街頭的快照,以及后來用大畫幅相機(jī)到美國南部拍攝的佃農(nóng)的生活狀況和肖像,是一部反映1930年代美國時代精神的視覺影像檔案。雖然肖爾從來沒有遇到過埃文斯,但他從埃文斯的照片中感覺到,自己與埃文斯“在視覺上相近”。

另一位對肖爾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藝術(shù)家是美國“波普藝術(shù)”主要代表人物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28~1987)。17歲時,肖爾曾在沃霍爾名為“工廠”的工作室拍攝這位藝術(shù)家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目睹了沃霍爾如何引導(dǎo)他的伙伴共同進(jìn)行創(chuàng)作,包括沃霍爾拍攝的一些實驗性電影,讓肖爾了解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關(guān)系到如何做決定,而且“目的性”(intentionality)要明確。換句話說,需要觀念先行。
1971年,肖爾創(chuàng)作的幾個系列觀念攝影作品在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展出,成為自美國攝影家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1864 ~ 1946)之后在該博物館舉辦個展的第二位在世攝影家。這些作品均具有“觀念性”,例如,題為《圓圈第一號》作品是肖爾站在一個曠野中按照東西南北不同方向拍攝的自拍像;另一個題為《24小時》的作品是肖爾每隔半小時用相機(jī)記錄他一天生活狀況的照片。
肖爾曾與另一位美國著名攝影家保羅·斯特蘭德(Paul Strand,1890 ~1976)共進(jìn)過午餐。他曾告誡肖爾不要用彩色照片進(jìn)行創(chuàng)作,因為他認(rèn)為,“有深度的情感無法用彩色來表達(dá)”。雖然肖爾十分尊重這位老攝影家,卻不敢茍同他的觀點。肖爾想到抽象藝術(shù)畫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色彩斑斕的畫作便能傳遞強(qiáng)烈的情感。于是,他在1971年開始嘗試用彩色照片進(jìn)行創(chuàng)作,尋找新的創(chuàng)作方向。
剛開始,他是受所收集的明信片中的照片啟發(fā),先是用簡易玩具相機(jī)拍攝,之后將它們送到柯達(dá)快照沖印店直接放大成5英寸照片。后來,他又用祿萊135相機(jī)拍攝如明信片式的彩色照片,送到專門印制明信片的工廠制作一組明信片,并寄放在書店銷售。這兩個系列作品為他后來創(chuàng)作的《美國表象》(American Surfaces)打下了基礎(chǔ)。
1972年,肖爾自駕車到美國各地拍攝“在路上”式的項目。出發(fā)前,肖爾的好友德國著名攝影家希拉·貝歇(Hilla Becher,1934~)曾建議他,要拍攝美國每一條著名的主要街道。但肖爾更喜歡拍攝他在旅途中經(jīng)過的美國不知名小鎮(zhèn)的街道,以及他所住過的每個旅館的床鋪、吃過的每一頓早餐,甚至馬桶、電視機(jī)、加油站、電影院、停車場和十字路口等日常的社會和文化景觀。

結(jié)果,他將這些快照式的照片分三排直接用圖釘固定在畫廊的墻上展出。由于肖爾的創(chuàng)作理念過于超前,就連當(dāng)時的一些攝影評論家也不得要領(lǐng)。但時任紐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攝影部主任約翰·薩考斯基(John Szarkowski,1925~2007)卻獨具慧眼,看出肖爾這部作品的意圖,并提示肖爾,通過135相機(jī)取景器與大畫幅相機(jī)取景器觀看世界的區(qū)別。這給肖爾提了一個醒。
從此,肖爾嘗試用大畫幅相機(jī)繼續(xù)上路拍攝。他先是用4×5相機(jī)后改用8×10大畫幅相機(jī)拍攝。因為大畫幅相機(jī)必須放在三腳架上拍攝,肖爾需要對畫面的結(jié)構(gòu)作出各種決定,或是思考如何將三維世界變成二維的畫面,或是在二維的畫面產(chǎn)生出三維的深度。這種拍攝方式使得肖爾的作品始終是在記錄具有時代色彩的社會和文化景觀,同時在探討影像畫面的構(gòu)成。
1976年,肖爾將這些大畫幅相機(jī)拍攝的作品結(jié)集成冊,題為《不尋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這部作品既反映了上世紀(jì)70年代“美國文化的真面目”,又注重色彩與畫面中其他元素的內(nèi)在關(guān)系,被視為“彩色攝影的經(jīng)典之作”。
1980年代,肖爾又開始挑戰(zhàn)自己,他從紐約搬到美國內(nèi)地蒙大拿州居住兩年,在拍攝了社會風(fēng)景之后,他又開始探索如何拍攝自然風(fēng)景。但他不是拍攝沙龍式的風(fēng)光攝影,而是探究如何能夠利用前景、中景和背景之間物體的關(guān)系,來引導(dǎo)觀者在平面的照片上看出現(xiàn)實世界的立體深度。進(jìn)入1990年代,當(dāng)彩色攝影被接受為藝術(shù)攝影的媒介之后,肖爾又轉(zhuǎn)向探討黑白攝影照片。肖爾一直是通過顛覆傳統(tǒng)觀念來探索攝影媒介的各種可能性。

各種可能性正在召喚
隨著本世紀(jì)電子和數(shù)碼技術(shù)的高速發(fā)展, 2003年,肖爾發(fā)現(xiàn)蘋果電腦公司在因特網(wǎng)上提供了一項根據(jù)客戶需求印制畫冊的服務(wù)。這種稱作iPhoto的應(yīng)用程序能讓用戶將他們拍攝好的照片存入該程序,并可利用該程序進(jìn)行排版,版面可以有不同的背景顏色、帶邊框或出血(不帶邊框)甚至跨頁等選擇,還能添加圖說和文字,而且能裝訂成不同尺寸和精裝及平裝兩種畫冊。用戶在排版結(jié)束后,直接上傳給蘋果公司,該公司會將印刷和裝訂好的畫冊送到客戶的家門。
肖爾意識到蘋果公司提供這項印制畫冊服務(wù)是又一個創(chuàng)作機(jī)會,便產(chǎn)生了利用這種應(yīng)用程序制作攝影畫冊的想法。在隨后的5年里,他用隨身攜帶的卡西歐、佳能或理光等傻瓜數(shù)碼相機(jī)和奧林帕斯數(shù)碼單反相機(jī)拍攝一些日常生活的專題,每個專題均在一天內(nèi)完成,一共制作了83本,每本限量20冊,在畫廊銷售或自行出售。最終由費頓出版社將這83本畫冊合訂出版為一本大型畫冊,名為《書中之書》(The Book of Books),共分兩冊,限量250本,每本定價2500美金。
這套畫冊的出版再次表明,肖爾畢生都在探索攝影媒介的各種可能性,并不斷推翻常規(guī),同時,又保持自己建立的攝影風(fēng)格。從這套畫冊每一個單行本可以看出,肖爾始終是在觀察現(xiàn)實世界所存在的視覺影像,并選擇一個專題進(jìn)行拍攝。例如,他到巴黎盧浮宮蒙娜麗莎名畫前拍攝觀眾使用傻瓜相機(jī)拍攝這幅名畫的手的姿勢和相機(jī)中的畫面;他利用自己乘坐的飛機(jī)降落前在地面上變得越來越大的倒影作為線索來拍攝窗外的景象;他在維也納舊貨市場拍攝各種正在出售的畫作和工藝品等。
2005年8月,肖爾看到《紐約時報》發(fā)表了關(guān)于美國發(fā)生卡特琳娜巨大風(fēng)災(zāi)頭條重大新聞報道之后,決定每逢《紐約時報》有頭條重大新聞報道,便會拍攝那一天的民眾生活狀況,作為他拍攝這套畫冊中的一個系列。由此可見,肖爾的拍攝項目總是基于某一種創(chuàng)作觀念。同時,他所拍攝的這些畫面仍然保持著在《美國表象》和《不尋常地方》項目中的方法,將鏡頭對準(zhǔn)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和文化景觀,而且他的照片總是充滿豐富的細(xì)節(jié)和觀看的樂趣。
他利用蘋果iPhoto應(yīng)用程序為他的作品尋找到新的呈現(xiàn)媒介,所制作的這套畫冊每一本本身就是一個藝術(shù)品,很快被許多收藏家收藏。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也收藏了他的所有83本畫冊。在當(dāng)下掀起攝影藝術(shù)家自行設(shè)計和制作畫冊熱潮之前,肖爾就已經(jīng)是弄潮兒?,F(xiàn)在他又轉(zhuǎn)向另一種創(chuàng)作媒介,這一回,他是利用iPad電子書的呈現(xiàn)形式和視頻媒介進(jìn)行創(chuàng)作。
2013年由菲頓出版社推出的《紐約一分鐘》電子書,是肖爾在他最熟悉的紐約市用松下攝像機(jī)拍攝的16個視頻組成。每個視頻均不超過一分鐘,是將攝像機(jī)放在三腳架上錄制而成。他沒有推拉鏡頭,也沒有切換鏡頭,更沒有配樂或旁白,也沒有現(xiàn)場的錄音,完全是像默片一樣,讓讀者自己欣賞觀看。
雖然這些視頻是動態(tài)影像,卻是從攝影家的視角拍攝。由于鏡頭沒有推拉和切換的變化,加上肖爾總是借助一些固定不動的物體,如人行道、廣告牌、十字路口、地鐵出口處、路邊的一灘污水等作為背景,同時讓行人、汽車、樹葉、影子、泡沫等的移動,來產(chǎn)生動靜結(jié)合的畫面。如果不是樹葉和門簾的影子不時在移動,其中有幾個視頻乍看起來完全像肖爾的靜態(tài)照片。因此,可以說,這些視頻是由一系列靜態(tài)影像組成的動態(tài)影像。

這些視頻各自獨立,同時又有一定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他們具有某些故事情節(jié),但沒有開頭也沒有結(jié)尾。不過,肖爾在編輯時,將不同車輛駛過斑馬線的視頻放在首位,并將三個在同一個地鐵出口處拍攝的視頻穿插在整本書中,中間還分別出現(xiàn)如同靜態(tài)照片的視頻與不斷有行人走到的視頻,以便使讀者產(chǎn)生閱讀的節(jié)奏和變化。此書還以一個路邊的熱狗攤販架設(shè)陽傘與一位中年職業(yè)婦女在辦公樓前吸煙的幽默視頻作為高潮,并將包含“各種可能性正在呼喚”的三星手機(jī)廣告詞畫面的視頻放在末尾,形成了這本書的松散結(jié)構(gòu)。
如同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1924~)利用汽車、留聲機(jī)、高速公路和美國國旗這些具有時代和文化含義的意象穿插在他的經(jīng)典畫冊《美國人》中一樣,肖爾也有意識地將黃色校車、黃色出租車、紐約地鐵站出口、意大利比薩餅店和街頭的熱狗攤販等具有紐約特征的意象記錄在他的視頻中,并且,還記錄了紐約不同族裔的行人,以及過于肥胖的美國人和大家普遍使用手機(jī)等時代的特點,共同構(gòu)成了一部關(guān)于這個時代紐約人剪影的電子書。
正如歐仁·阿杰(Eugène Atget,1857 ~ 1927)在二十世紀(jì)初記錄即將消失的老巴黎時,沒有去拍攝埃菲爾鐵塔,也沒有拍攝凱旋門一樣,而是用警察記錄犯罪現(xiàn)場的方式,盡可能客觀記錄巴黎老城區(qū)中的街道、大門、公園和櫥窗,肖爾也是繼承了這種“紀(jì)實性”的傳統(tǒng),他沒有拍攝帝國大廈和時報廣場等紐約的標(biāo)志性建筑,而是將鏡頭對準(zhǔn)紐約日常生活的細(xì)微畫面。如同安迪·沃霍爾已成為經(jīng)典的實驗性電影一樣,肖爾拍攝的這些視頻很可能也會成為經(jīng)典。
目前,肖爾又完成一部用尼康D800相機(jī)的錄像功能拍攝的視頻電子書,該項目將會持續(xù)一段時間。近年來,他還到以色列、烏克蘭和阿聯(lián)酋等國創(chuàng)作新的攝影項目,不斷給自己提出新的挑戰(zhàn),以便進(jìn)一步超越自己。在肖爾看來,各種可能性正在召喚,攝影媒介的可能性是無窮的。





 首頁
首頁 來源:瑞象館
來源:瑞象館 責(zé)編:撰文:江融
責(zé)編:撰文:江融 2015-01-06
2015-01-06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1020008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102000847號 掃碼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掃碼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掃碼關(guān)注官方微博
掃碼關(guān)注官方微博 各團(tuán)體會員微信公眾號集成平臺
各團(tuán)體會員微信公眾號集成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