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正在法國舉辦的阿爾勒國際攝影節(jié)上,中國著名攝影理論家藏策作為受邀專家,在攝影節(jié)上做了《從巴特到“元影像”》的演講,得到了國際學(xué)者們的高度評價。法國學(xué)院書籍與知識部副主任朱笛特·郈茲稱藏策是一個給他們帶來了震驚的學(xué)者。學(xué)術(shù)活動負(fù)責(zé)人娜塔莉·拉括認(rèn)為藏策對羅蘭·巴特符號學(xué)思想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讓法國的符號學(xué)有了中國的維度。法國學(xué)者、羅蘭·巴特研究專家馬修·麥塞哲說:在這個“巴特又回來了”的主題中,我們看到巴特也從中國回來了——法國符號學(xué)經(jīng)過中國理論家的改造,今天又“回家”了。
巴特對于攝影的分析,其實更多是從普通的私人家庭照片,以及新聞?wù)掌?、廣告等切入的。藏策在講演中對此認(rèn)為,巴特對于攝影領(lǐng)域的這種偏重個人感受式的介入,卻更加促進(jìn)了攝影向著另外一條路徑的轉(zhuǎn)向。以往的攝影,主要是攝影師沿著對影像自身的探索而進(jìn)行的,所謂的攝影理論,也主要是對于攝影經(jīng)驗的歸納。比如安塞爾·亞當(dāng)斯的“區(qū)域曝光理論”、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決定性瞬間理論”等等。而巴特對于攝影的探索方式則與他們不同,巴特是站在影像之上的層面上來分析影像的。而這種來自巴特的符號學(xué)方式,給正日益受到觀念藝術(shù)等思潮影響的攝影師們帶來了新的啟示。攝影發(fā)展的路徑由對影像本身的探索,過渡到了由學(xué)術(shù)及理論所引領(lǐng)的攝影實驗。這也正是巴特之于攝影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于為何把巴特的藝術(shù)思想作為自己攝影理論研究的重心,藏策表示,在上個世紀(jì)的80年代,巴特是隨著各種西方文藝?yán)碚摰囊M(jìn)而被介紹到中國的,此后逐漸在中國的知識界聲譽日隆。然而直至今日,中國學(xué)者對巴特的研究仍主要在譯介和闡釋的層面上進(jìn)行,卻很少有人能在巴特之后繼續(xù)推進(jìn)他的各種思考。這種狀況讓他想到了古代中國對于佛學(xué)的發(fā)揚光大與“倒流”回印度的盛況。今昔對比實在令人汗顏!于是他選擇了在漢語的世界中繼續(xù)推進(jìn)巴特式的思考。他表示,自己的理論靈感已不僅僅來自巴特,同時也參考了格雷馬斯、雅克·拉康以及??碌热说睦碚摗K?001年發(fā)表了以《攝影·批評·文化研究》為總標(biāo)題的六篇論文,第一次將符號學(xué)的方法應(yīng)用于中國的攝影理論研究。其后他又提出了“元影像理論”(théorie de la méta-image),并與中國的攝影師們一起進(jìn)行了多次頗具影響的影像實驗。
阿爾勒國際攝影節(jié),是世界上創(chuàng)辦最早、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節(jié)之一。藏策是首位受邀在這個攝影節(jié)上做學(xué)術(shù)演講的中國理論家。近年來,中國攝影發(fā)展迅速,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攝影家參與國際交流也日益頻繁,但中國的攝影理論研究卻一直未能走向國際。藏策受邀在阿爾勒攝影節(jié)的演講,是中國理論家第一次走上國際講壇,是中國攝影理論步入國際學(xué)術(shù)界的一個良好開端。來自韓國的著名策展人宋修庭女士也來到了阿爾勒,向藏策表示祝賀。
藏策是我國的著名文學(xué)與藝術(shù)理論家,曾獲中國攝影金像獎(理論獎),以及濟(jì)南國際攝影節(jié)“最高學(xué)院獎”等多項大獎。他的藝術(shù)符號學(xué)研究方法源自法國學(xué)術(shù),但又經(jīng)過了他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加入了源自東方智慧的維度。他創(chuàng)建的“超隱喻理論”和“元影像理論”,在國內(nèi)有著很大的影響。連續(xù)兩屆的濟(jì)南國際攝影雙年展,就都是以“元影像理論”作為學(xué)術(shù)框架的。“元影像理論”還引領(lǐng)了一系列的影像實驗活動,如《隱沒地》影像實驗,就曾為包括央視在內(nèi)的國內(nèi)300余家媒體報道,形成了廣泛的影響力。由藏策作學(xué)術(shù)主持的“乾坤灣影像實驗”“華山新風(fēng)景影像實驗”等也都是近年來中國攝影界中的亮點。藏策個人的觀念攝影作品《格林威治時間》,也在廣州、西安、寧波等地參加了巡展。#p#副標(biāo)題#e#
從巴特到“元影像”
女士們先生們:
諸位好!
我是來自中國的藏策,我在我的國家,在漢語的世界里,一直繼續(xù)著羅蘭·巴特式的符號學(xué)研究工作,繼續(xù)著他對影像奧秘的探索。非常高興在阿爾勒與諸位相聚!
我們這個工作坊的題旨“巴特回來了”,讓我聯(lián)想到了巴特在《明室》中,對于他母親生前照片的精彩分析,對于當(dāng)時的巴特來說,在凝視母親照片的那一刻,他的母親也“回來了”。巴特因而也確信:“攝影真諦的名字是‘這個存在過’ (ça a été)”。而剛剛馬修先生則對我說,你的研究表明,巴特也可以從中國回來。
巴特對于攝影的分析,其實更多是從普通的私人家庭照片,以及新聞?wù)掌V告等切入的。他在《明室》的《私生活/公眾生活》章節(jié)里甚至說:“業(yè)余愛好者通常被說成不成熟的藝術(shù)家:一個不能——或不愿——上升到專業(yè)水平的人。但是,在攝影活動領(lǐng)域里卻相反,達(dá)到專業(yè)頂峰的往往是業(yè)余愛好者:離攝影真諦最近的,正是這種沒有上升到專業(yè)水平的人。”所以在這里,我也要向大家展示幾張由完全沒有經(jīng)過攝影訓(xùn)練的中國農(nóng)民拍攝的照片,希望大家能從中發(fā)現(xiàn)“刺點”。這些照片源自我們在中國進(jìn)行的一個影像實驗,由數(shù)十位藝術(shù)家與當(dāng)?shù)剞r(nóng)民共同參與,農(nóng)民拍攝了大量精彩的照片,這幾張只是其中極少的代表。
下面讓我們繼續(xù)來討論巴特,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巴特對于攝影領(lǐng)域的這種偏重個人感受式的介入,卻更加促進(jìn)了攝影向著另外一條路徑的轉(zhuǎn)向。細(xì)細(xì)想來,這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是攝影界對于巴特的一種很奇妙卻又富于創(chuàng)建性的誤讀(lecture fausse)。以往的攝影,主要是攝影師沿著對影像自身的探索而進(jìn)行的,所謂的攝影理論,也主要是對于攝影經(jīng)驗的歸納。比如安塞爾·亞當(dāng)斯(Ansel Adams)的“區(qū)域曝光理論”、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HenriCartier -Bresson )的“決定性瞬間理論”等等。而巴特對于攝影的探索方式則與他們不同,巴特是站在影像之上的層面上來分析影像的,他所探討的其實是有關(guān)影像的影像(我稱之為“元影像”: méta-image)。而這種來自巴特的符號學(xué)方式,給正日益受到觀念藝術(shù)等思潮影響的攝影師們帶來了新的啟示。攝影發(fā)展的路徑由對影像本身的探索,過渡到了由學(xué)術(shù)及理論所引領(lǐng)的攝影實驗。這也正是巴特之于攝影的重要意義所在。不過在我看來最為有趣的是,以學(xué)術(shù)與理論為核心的攝影路徑,最終卻又挑戰(zhàn)了巴特所謂“這個存在過”(法文原文:ça aété)的攝影真諦。尤其是在被稱為“后攝影”時代的今天,各種“不曾存在過”的虛擬影像正在顛覆并超越巴特當(dāng)年對于攝影的認(rèn)知。這大概是巴特當(dāng)年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理論研究者和藝術(shù)家,接下來我想說一下巴特在中國的影響以及我本人所受到的啟發(fā)。在上個世紀(jì)的80年代,巴特是隨著各種西方文藝?yán)碚摰囊M(jìn)而被介紹到中國的,此后逐漸在中國的知識界聲譽日隆。然而直至今日,中國學(xué)者對巴特的研究仍主要在譯介和闡釋的層面上進(jìn)行,卻很少有人能在巴特之后繼續(xù)推進(jìn)他的各種思考。在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攝影的批評界,人們對于符號學(xué)以及各種話語分析理論仍然感到陌生。這種狀況讓我想到了古代中國對于佛學(xué)的發(fā)揚光大與“倒流”回印度(le retour àl’Inde)的盛況。今昔對比實在令人汗顏!于是我選擇了在漢語的世界中繼續(xù)推進(jìn)巴特式的思考。當(dāng)然我的理論靈感已不僅僅來自巴特,同時也參考了格雷馬斯(A.J. Greimas)、雅克·拉康(JacquesLacan)以及??拢∕ichel Foucault)等人的理論。
我于2001年發(fā)表了以《攝影·批評·文化研究》為總標(biāo)題的六篇論文,第一次將符號學(xué)的方法應(yīng)用于中國的攝影理論研究。首先,我將攝影視為一種“提喻”(synecdoque)。這既是針對攝影對空間的抽象而言,也是對其時間性的維度而言的,就如巴特所說“時間被卡住了脖子”(法文原文:“leTemps est engorgé”)。在這些文章中,我受巴特有關(guān)“神話”(mythe)論述的啟發(fā),又參照了解構(gòu)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超隱喻理論”(théorie del’ultra-métaphore)。這是一種專門分析漢語中權(quán)力話語編碼的理論,涉及到文學(xué)與藝術(shù)的“元語言”分析(analyse métalinguisque)。這些文章后來結(jié)集為《超隱喻與話語流變》(Ultra-métaphore et flexion du dixcours)一書。其后我又提出了“元影像理論”(théorie dela méta-image),并與中國的攝影師們一起進(jìn)行了多次頗具影響的影像實驗。
就如巴特在《明室》中所言:“影像的本質(zhì)全然是外在的,沒有內(nèi)心的東西,但它比最深層次的思想更難接近,更加神秘;它沒有意義,卻又能喚起人的一切感覺所能有的最深切的東西……”而我個人則認(rèn)為:攝影本身只是一種現(xiàn)代科技的媒介,在攝影的層面上是解決不了攝影問題的,需要在觀念的層面上解決;而觀念本身又解決不了觀念的問題,需要在哲學(xué)的層面上來進(jìn)行思考;可哲學(xué)也同樣無法尋得所謂的“真理”,哲學(xué)不過是一種認(rèn)知的方式而已,所以哲學(xué)的問題又需要在思想的層面上來解決;而真正的思想是源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在靈魂的層面上進(jìn)行。這正是“元影像理論”(théorie dela méta-image)的一個基本思路。
我們知道,巴特在晚年對古老的東方智慧頗有會心,在他開設(shè)的《中性》(Le Neutre)課程中借助了中國的道家思想來闡述他的“中性”。在此我也想說一點我個人在消弭二元對立(opposition binaire)方面的心得。在我看來,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對立,就是文明與反智(contre-intellectuel)的對立。然而反智其實又恰恰是文明的”影子”( ombre)——因主流文明的壓抑而得不到分化與發(fā)展的結(jié)果。所以,縱觀歷史上的種種紛爭,也只不過都是人類在與自己的影子作戰(zhàn)。
謝謝諸位!#p#副標(biāo)題#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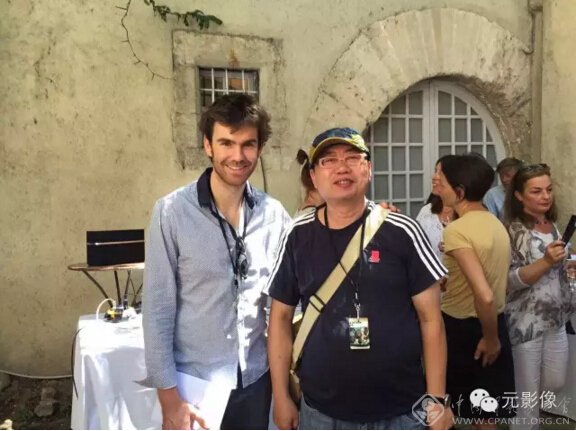
藏策對馬修先生的回應(yīng):
馬修先生引用了巴特的話:“一種影像,從本體論上說,就是什么也不能說:為了談?wù)撚跋?,必須有一種非常艱難的特殊技藝,影像描繪技藝”。
我也引用巴特的兩段話,來說說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巴特說:“在照片的情況里,因為——至少是在文字訊息的層次上——所指與能指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屬于‘轉(zhuǎn)換關(guān)系’,而是屬于‘記錄關(guān)系’,并且無編碼顯然在增強照片的‘自然性’的神話:場面在此,它是機械的但非從人的方面來被獲取的(機械性在此是客觀性的保證);人對于照片的介入(取景,距離,燈光,朦朧,運動線條)都屬于內(nèi)涵平面;一切就好像在最初(即便是空想的最初)就有一幅毛坯照片(正面的、清晰的照片)那樣……”(這段文字見于巴特《顯義與晦義》原文【L'obvie et l'obtus】,p. 35)。
此外巴特在《明室》下篇36節(jié)里比較了語言文字(說)與攝影的不同:“這種肯定性,任何文字的東西都不能給我。自己不能證實自己,是語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語言的樂趣所在)。語言的本質(zhì)可能就是這種無能為力?;蛘?,用肯定的方式說:語言從本質(zhì)上說是虛幻的;為了使語言變得不虛幻,必須采取一大套手段:要求助于邏輯,或者,如果不合邏輯,就求助于誓言。但攝影對任何中介物都不感興趣:它不創(chuàng)造什么;她就是證明的化身。”
至于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如果將哲學(xué)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廣義語言觀,引入到我們的討論中,問題就會變得明晰起來。阿多諾認(rèn)為:“整個自然也充滿了無名的未曾言說的語言。”人的語言是對事物的語言的翻譯,把事物的語言翻譯為人的語言不僅僅是將無聲的翻譯為有聲的;而且也是將無名稱的翻譯為有名稱的。那么攝影則是將事物的語言的痕跡留在了照片上,其不可被人類語言所轉(zhuǎn)譯的恰恰是真正屬于攝影的,而這也正是其不可說的部分。
2015年7月8日下午
于阿爾勒國際攝影節(jié)“巴特又回來了”學(xué)術(shù)主題工作坊



 首頁
首頁 來源:《中國藝術(shù)報》
來源:《中國藝術(shù)報》 責(zé)編:黎語
責(zé)編:黎語 2015-07-24
2015-07-24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1020008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102000847號 掃碼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掃碼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掃碼關(guān)注官方微博
掃碼關(guān)注官方微博 各團(tuán)體會員微信公眾號集成平臺
各團(tuán)體會員微信公眾號集成平臺